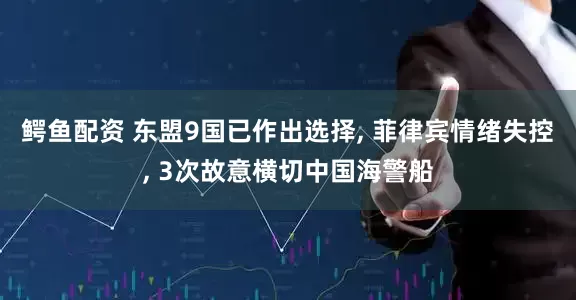本文刊登于《ELLEMEN睿士》6月刊卷首高开网

高铁靠站了,我起身下车,身周还坐着的乘客中飘来话音,“这个地方的鸡腿很有名哟”。
走在站台,沐进老家的晚风,身体立即松缓下来。这里的空气质地我如此熟悉,有独特的气味和湿度,它会瞬时反应在我细软头发的状态上。这点很奇怪,去任何其他地方,我的洗漱包里都会装好自己用习惯了的洗发水,但回老家就不需要。爸妈用的随便什么洗发水,二合一,霸王防脱,何首乌,我跟着用,头发都蓬松柔软、根根分明。我想这家乡的水就是好,没的说。
在上海下了班搭高铁,两个半小时到老家,这个时间点的夜色,我也很熟悉。4月末尾,春未尽夏还凉,天色墨蓝而清透,云没有,星光疏淡,一点点尘土、花香和食物夹杂的味道荡在鼻子里——这里头肯定没有卤鸡腿的味道,本地人才不爱吃这个。
我老家,自古交通便利,“四省通衢”,那些年,定是商贩们捣鼓出这个便于在车站铁道边操作的美食商业点子,挣过往旅客的钱。挺厉害的,靠口碑,也算成为早期网红地域特产了。
要好的高中同学在出站口接上我,开车带我去吃好吃的,给我“补补”,“瘦成什么了”,“馋了吧?想家乡菜了吧?”……这条路线,这种形式,这些言语的碎片,都那么熟悉,多少年了一直在重复,已经成为一种我人生惯例的组成部分——包括桌上那些我爱吃的菜,也一直重复,无法改变。
爆炒螺丝,加了紫苏叶子或薄荷叶子的。
炒鸡爪高开网,炒青蛙,后面这个自己小时候钓来吃,现在不能吃了,田野的好朋友,要保护。
冬天吃炒油菜(油菜花的嫩苗,红色),夏天吃炒地瓜叶,蔬菜里都放辣椒。
豆豉煎辣椒(也就是外地人认为的辣椒炒辣椒)。
近些年又引进的新菜色是红烧臭鳜鱼,香辣小龙虾。
点心主食是各种米粉,本地特产的弋阳年糕、饭麸果、芋头果、荞麦饺(里头包辣萝卜丝)。
关于中国人吃辣的地域性特点,我自己深刻揣摩过。我老家虽是江西,但地处浙江与江西交界,它的辣和中心赣菜的辣不同,应该偏向于浙江衢州菜的那种风格——学古代汉语时发现老家方言属于吴方言,是为依据之一。
相比湖南的干辣、四川的红油麻辣,老家的菜是一种入味咸辣。小炒居多,因而菜料多喜切小切碎,一份菜的配料和主料几乎一样多。我看我妈做饭就这样,姜、葱、蒜、小米辣椒、芹菜、蒜叶、榨菜、梅干菜这些配料,每样都切碎各搁一碗摆一摊子,做个肉类大菜,顺手在每个碗里抓一把配料往里撒。一顿餐,盘子里鱼和肉吃完了,剩下的配料不能收走,舀几勺浇在饭上,更够味,还能扒下两碗呢。
一个人在童年原生地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其一生,这是肯定的。偏甜的上海菜,至今我都不大沾,初次目睹著名的“排骨年糕”,那年糕竟然和饼那么大,着实吃了一惊。吃惯了小炒的我,对于大块的红烧肉,大块的牛排,大只的馄饨,依然是看一眼就觉得饱,只一口就算交代了。多年来自己叫的外卖,不是米粉凉皮臭豆腐,就是麻辣烫麻辣香锅红油串串,俱是某种代替品,代替着胃口的乡愁。
同学们陪着我大快朵颐,聊聊天,灌下一两瓶啤酒,到深更半夜再把我扔回家。自己开了密码锁进去洗漱歇息,睡一觉醒来,从我的小房间出来再和爸妈打招呼,“你起床了”。“嗯,我回来了”。这也成惯例。
爸妈的早午饭通常是粥,但会专门给我备上米粉,有时候是市场买的新鲜粉,自己配了肉料(猪肝、碎肉或小排小肠)给我煮,有时就去小区门口的米粉店给我端一碗现成的。假如我一天都不出门,这第一顿之后,午饭十一点半,晚饭下午五点半,就会极其规律准时地喊我吃。我在家的常态就是被喊出房间,拍着肚皮,一脸苦笑,“又要吃饭了?”
很早以前,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妈说过,许多家里的独门菜,在我妈之后可能会失传,我让她把菜谱和做法写下来交给我继承。我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,不过,“你真的会做吗?”“你写出来了我以后肯定能做的。”我拍着胸脯答应过。我不光想继承我们家的美食,以后还想跟着她打太极。据我多年观察,我妈寒来暑往不间断地打太极,从小区太极女王打到拿下省级一等教学证书,七十岁了还是黑发童颜,身手不凡,可见打太极定然对身体大有好处。
弄吃的和打太极是我妈在如今的生活中最看重的两件事,在这两件事上追随她赞美她,最能哄她开心。儿女必须深谙此道。我爸持重深沉一些,相对没那么好哄,但看着我踏实吃饭,听我说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,他也是极为开心的。每次短暂的相聚后,再送我出门,他们也就念叨那简单的一句:好好吃饭,注意身体——我知道,天下父母心,其实就在这一句。
假期后回到上海,我突然不想吃外卖了,开始坚持去社区食堂吃饭。骑着单车往湖南路去,初夏的梧桐树遮出浓荫,米黄色的拱门上垂着爬山虎,一切清清静静的。食堂里菜色丰富,荤素搭配,价廉物美,还能不时换着吃面和馄饨。每吃一顿,我就拍个照片给爸妈看,妈妈喜欢看图猜菜,再发个玫瑰花,爸爸就回复大拇指,很多很多个大拇指。
我会好好吃饭。这也许才是母亲节或者父亲节,我们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。

编辑总监 何叶
尚红配资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